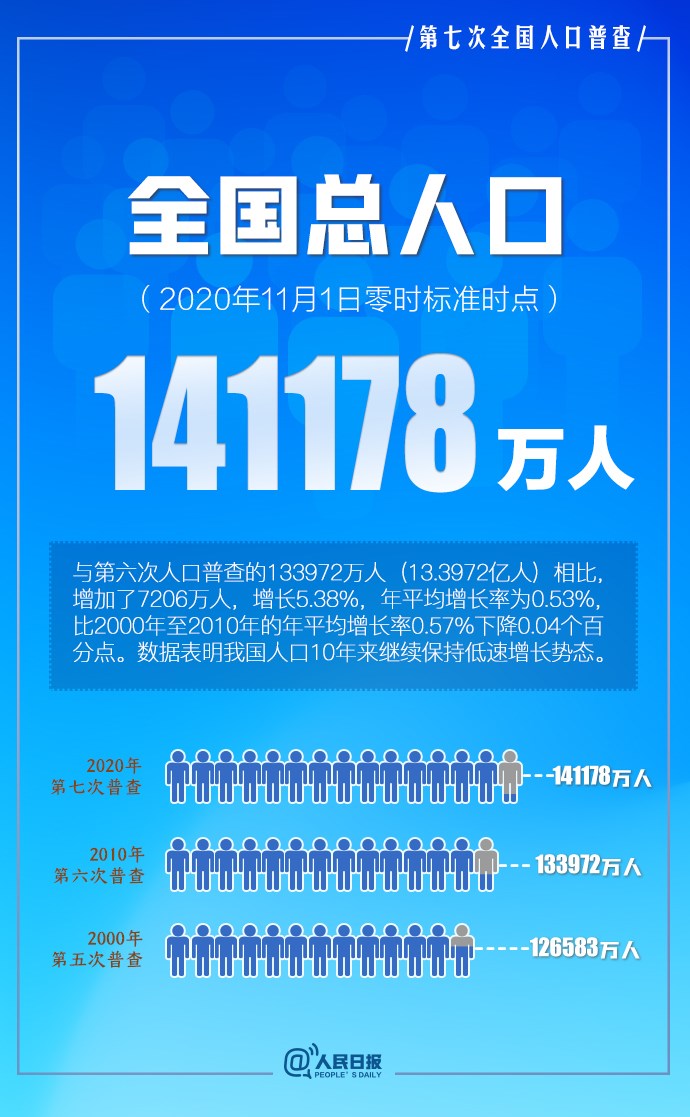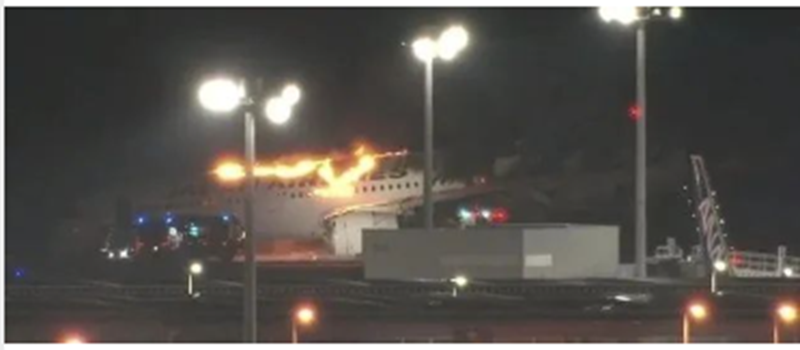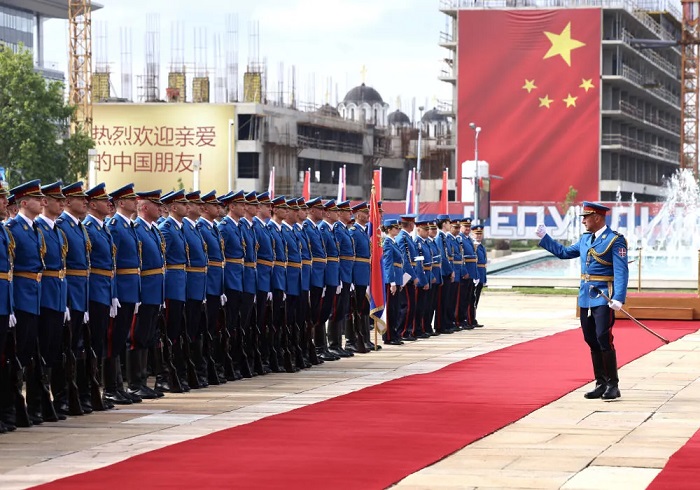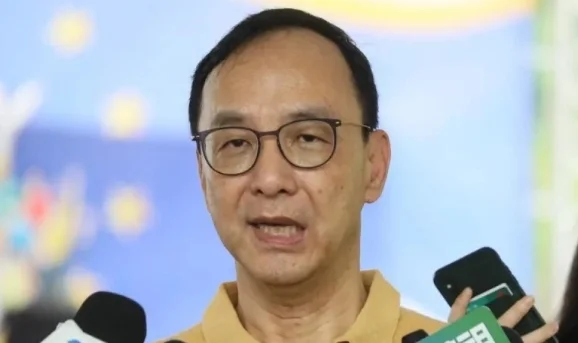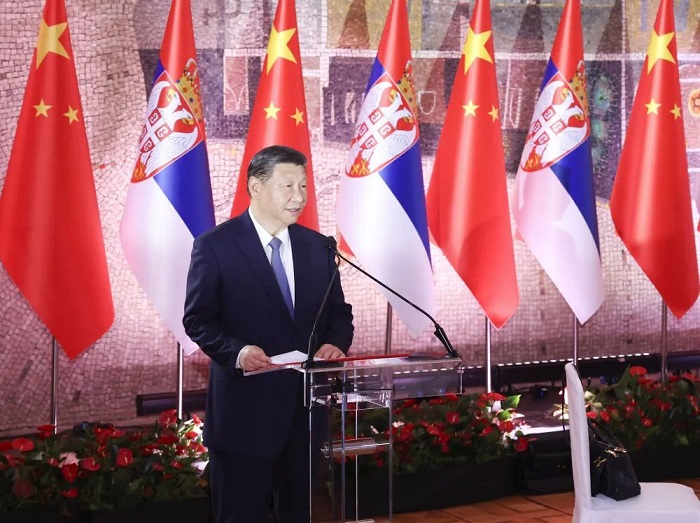寻找母亲
文/严风华
人一老,就变得可怜。
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单位时,见满院子都是作家、艺术家。他们意气风发,满腹经纶,各领风骚。转眼我人到中年,他们纷纷退休了。似乎转眼的功夫,个个白发苍苍,有拄拐棍的,有坐轮椅的,全然不见当年的风姿。有的甚至乘鹤西归,作古了。
人一老就让人操心。比如我父母。他们都七十多岁了,家住市郊十多公里处。我们兄妹四人,平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去。父亲是书呆子,一天到晚只顾读书,母亲只好操持家务,买菜煮饭菜一人包了。但自今年初以来,母亲手脚就开始不太灵便了,煮饭菜的活都由暂时跟他们住的三弟、三弟媳做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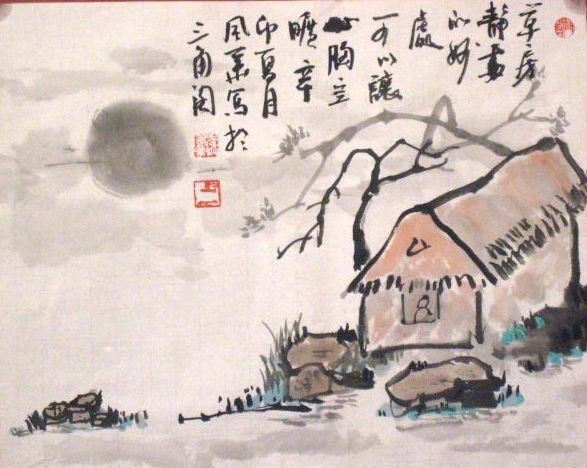
我就想,是不是请个保姆,帮助他们打理生活。可父亲说不用,他们还能自己照顾自己。
但人毕竟老了。他们总有动弹不了的那一天。还有,他们将无法避免地相继离世。那么,谁来照顾最后的父亲或母亲?
这些事情,以前是不会考虑的。人到中年,就不得不瞻前顾后了。
也许是想多了,事情真的发生了。
前些天一个下午五点多钟,妹妹打来电话,说母亲出来找我,问我她在不在我这里?我说不在。
我连忙跑到大门问门卫,门卫说没见着。
母亲是三点多出门的。至今已有两个多小时,按理已经到达。这只能说明,母亲失踪了。
今年初开始,母亲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症状。不与人交流说话,行动迟缓,容易健忘。下楼散步或买东西,好几次都迷路找不着家。
我立即给弟妹打电话,发动大家找。二弟是警察,他立即给附近的几个派出所通报,帮助寻找。或留意今晚是否出现老人失踪的报案。
匆匆吃过晚饭,我和妻子开着车沿着平常父母外出乘坐的公车线路寻找。那时夜幕已经降临,到处灯火灿烂,人影憧憧。我不会开车,是妻子开车。我们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两旁的人行道。她负责看左边,我负责看右边。可哪里是母亲的身影啊?
寻找母亲,这样的感觉怪怪的。相信大多数家庭,在正常情况下,只有父母寻找孩子的份,没有孩子寻找父母的。我就曾因为孩子放学迟归而惊恐万状地去寻找过。担心她被拐或被歹人所欺。母亲不用担心这一点,就担心有什么闪失而造成不幸。
意外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对于意外的发生,可以作出多种设想。
任何一种设想都是有理由成立的,都是可怕的。作为设想者,在那种特定的时刻,总愿意把事情往最坏处想,这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意外,为意外做好各种思想准备,更是出于对处于危机中的亲人的思念、担心、牵挂。所以,我在寻找母亲的路上,总被各种设想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充斥着,压制着,难以开怀。
母亲,此刻你在哪里?你是不是因为找不到我而焦躁不安?或是因为迷失了返家的路而恐慌不已呢?
寻找母亲,第一次这样的经历实在闹心。
忽而一想,而作为母亲,一生当中则要经历多少次寻找的折腾啊!
我亲历过母亲那几次惊心动魄的寻找。
在老家读小学的时候,有一天中午,久久不见二弟回家。直到下午离上课时间还差半个小时,母亲急了,立即叫上我跟她去寻找。
我们住在小学校园里。附近有一条季节性的小溪流。每年七月份,不知哪一天突然来了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雨,第二天,水沟里就长满了浑浊的溪水。不久,水清了,鱼也来了,我们就到水面宽、水底深的地方游泳、钓鱼。那天,母亲带着我,边走边问我:二弟是不是游水被淹了?你们平时喜欢在哪游水?
我就直径把母亲带到我们常常游水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的水沟有一个拐弯,所以水深,水面宽,水流也急。站在岸边,看见水面清得泛绿,但漩涡涟涟,深不见底。母亲说,我不会游水,你下去捞吧。
那是一片我十分熟悉和喜欢的水域。每天吃了晚饭,我和弟弟以及邻居的玩伴总是要到这里游水。在水里,我们像泥鳅一样滑溜,像鱼一样欢快。水的清爽和凉快常常让我们忘记归家。但此刻,我突然对这片水域产生了恐惧与反感。但不得不按照母亲的指令下了水。我每走一步,水就漫上来两寸,顿时浑身冰凉,鸡皮疙瘩骤起。踩着了草根或石块,脚尖总得惊秫地抽搐一下,以为是踩到了二弟的身体。我十分麻木地用脚在水底里探了个遍,然后又潜到水底睁开着眼寻了个遍。我担心我万一看见了弟弟而不知道有没有胆量和力气把他拉上来。好在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二弟是贪玩忘了归家。
我们学校宿舍有两排房子,一排是瓦房,住人,一排是茅草房,做厨房。各家各户各分得一间。我家在第一间,是出入宿舍的必经之路。有一天下午放了学,我一放下书包就立即煮饭。每天都这样,我先煮饭,等母亲回来了再煮菜。可那天母亲迟迟不回。我就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鸡打架。
太阳刚刚下山的时候,我远远看见母亲回来了。她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。走近了看,是外公家那条街上的亲戚,有三姑,有六婆。母亲走在她们前面,个个行色匆匆,表情严肃。尤其是母亲,脸色铁青。当她们一眼看见我时,都齐齐都喊:呐!那个崽不是在这嘛,吓得我们鬼魂都散!我母亲的动作最为夸张,不断地拍打着胸口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那身架软塌塌的几乎要散。
原来,那天有个小孩,趁着拉甘蔗的卡车爬坡车速慢,就跑上去拉扯车上的甘蔗,不小心跌倒在车轮底下被压死了。听说那个小孩的母亲姓邬。我妈就姓邬,在整个县城姓邬的人没几个。母亲当时正在外面办事,一听到这个消息,立即拉上这几个三姑六婆赶回家看个究竟。结果见我好端端的活着,哭笑不得。
后来得知,那个死去的小孩的确就是我表姨的孩子。他们家是农家,每年都种有甘蔗。年年都给我们家送甘蔗。
母亲常说,你们别惹我生气,我每生气一次,就会死很多细胞。母亲为了寻找我们,那死了多少细胞啊!
母亲为我经历过一次最危险的寻找。
那时我已经读了初中。我常常在星期天和一些同学到野外砍柴,以补贴家用。但他们都有独轮车,我没有,都是用肩挑。肩挑不仅肩头痛,还挑得少。实在不甘心,我就让在乡下插队的表哥帮我砍来了两根木条,花了一个多星期,独自做了一辆独轮车。那时我已经学会做一些木工了。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,不可能保送上大学或招工,父母就打算让我做木工。这种工,也算是技术活,且不用日晒,不怕雨淋。
有了独轮车,我就和同学结伴去砍柴。这一次去的地方是一个叫黄茅岭的大石山,离县城有十多公里。入山越深,柴就越多。下午五点多,我们就装车出山了。但还没走出公路,我的车轮胶就脱落。我是用一个废弃的旧菜板做的轮子,根本没法固定车轮胶。同学看见了,却没有一个停下来帮忙,一个个嗖嗖地从我的身边走过。我只得请他们回去的时候务必告知我父母一声,让他们来接我。
好不容易将车推上公路。那时的公路都是沙石路,摩擦大,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。没多久天就黑了,我又饿又乏。实在坚持不了,只得将车子推到路边的草丛里藏好,做好记号,然后取下饭盒和柴刀,独自回家。
那时的野外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,几乎遇不到路人。当时是夏天,萤火虫忽隐忽现地在路边闪着丁点白光,来去无踪。我没见过鬼,但估计鬼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不容易有一两部手扶拖拉机突突突的路过。我招过手,但没有一辆给我乘搭。
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,仍然没见父母来。我开始觉得着急,后来就变成了埋怨甚至愤怒:这么晚了,你们也放心让我一个人在野外啊!?
走着走着,我流泪了。我已经不害怕黑夜,但我害怕渐渐漫上心头的那种被父母抛弃、没人在乎的感觉。
终于,黑暗中看见有一辆自行车迎面驶来。突然,我听到了一个女子说话的声音。我的心跳了一下,毫不犹豫的喊了一声:“妈!”
“哎!”那个女子立即回应了一下,从那辆自行车的后座上跳了下来。
是母亲。她那清脆的声音,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辨认出来。
黑暗中,我们彼此迎面走去。
原来,我那些不懂事的同学并没有告诉我父母。天黑了,母亲见我久久未归,实在放心不下,饭还没吃就出来找我了。
十多年后,我和母亲无意中谈起此事。她说,那天她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砍柴。只好胡乱选择了一个方向去找。一路上,她觉得走得太慢,就不断地拦截路过的手扶拖拉机,但就是没有一辆停下。最后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,母亲十分冒险地请求那男子给她搭了一段。她说,如果找不到我,她将一直走下去,走下去……
天啊,母亲如果不说,那将是一段烂在心底里的故事。那晚,母亲要是找不到我而一直走下去,那将会发生什么状况呢?如果那个男子起了歹心,那将是怎样的结果呢?
在特殊情况下的寻找,总是牵肠挂肚而充满危险的。
而今天,我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出门找我,这又是为了什么呢?
南宁的夜晚,总是很热闹的。汽车、自行车在路中疾驰,路人则在路灯下慢悠悠的走,各有各的心情。但恐怕没有谁如我们那样充满焦虑。我们的目光专门往老者身上瞄。每当看到行动迟缓的老者,我就希望那是就母亲。但总是失望。人海茫茫,谁知道母亲是在哪个角落呢?此时是十一月,南宁早晚凉,白天热,母亲出门时肯定穿着单薄,她会不会正躲在哪个角落打哆嗦呢?出来这么久,还没得吃饭,不知身上带不带钱,懂不懂得买东西吃?找不到我,又忘了回家的路,是不是害怕了?最要命的是,母亲尿频,在家时,每隔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,那么,在大街上她能找到地方方便吗?
沿着大街走了一圈,实在没辙,我们只好返回了。妹妹说,她在母亲家附近的几所大学校园里打着电筒找了,也没找着。
我们只好等,等派出所的消息。
晚十一点,我的电话响了。是一个陌生的电话。果然是警察。他说,你妈迷路了,我们送来了,你赶快回来接。
我赶紧从岳父家赶回单位,看见母亲安静地坐在门卫室门口的椅子上,微微地笑。警察说,还好,她还记得你的名字和单位。谢过警察,等他们走了,我便无奈地指着母亲说,你呀你呀,知不知道我们找你找得很苦啊?母亲却像个孩子似的,微笑着,有点不好意思。
还好,母亲身上穿着很厚的上衣。但裤子却很单薄,脚穿拖鞋,手里攥着一个矿泉水瓶和一只白色塑料袋;瓶子里已经没水了。塑料袋里装着几颗核桃仁。
我的宿舍就在单位的院子里。把母亲带回家,正好有面包,母亲是一阵狼吞虎咽。随后我问,你找我干嘛。她说,你不是要找什么电视报吗,我帮你找着了。
我什么时候要她找啊,何况她手里并没有任何报纸。
她肯定是因为一时迷糊才做出这样的举动。
我觉得做孩子的很幸运。我们这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都不怕丢失,因为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个人在寻找我们。
人的一生,是不是在亲情的寻找过程中完结的?
过了几天,我给一直在学校寄宿、忙着高考的女儿打了个电话,说,你有空回来看看奶奶吧。
她也许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。